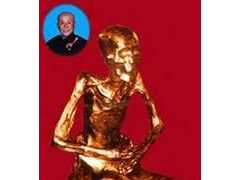弗朗西斯·雅姆这个名字念起来很是拗口的外国诗人,我没有去了解他更多的故事,我倒是很喜欢他的一首诗作《为他人的幸福而祈祷》:
天主啊
把我能拥有的幸福给予大家吧
愿喁喁倾谈的恋人们
在马车、牲口和叫卖的嘈杂声中
互相亲吻,腰贴着腰/愿乡村的好狗/在小旅馆的角落里
找到一盘好汤
睡在阴凉处/愿慢吞吞的一长溜羊群/吃着卷须透明的酸葡萄。
平白的诗中,诗人用一颗感恩的心在为人们及一切生灵祈祷,这不是教堂里简单意义上的祈祷,超越诗句以外的是他企望人类能生活在一个人畜共处的祥和环境中共享快乐。青年作家苇岸也很喜欢这首充满挚爱的诗,他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作家,他敬畏大自然,钟爱农耕文明,在他优美动人的散文中总是流淌着荒流溪水的清韵,草木野花的芬芳,小鸟蜂蝶的迷影,他一颗宁静的心时刻为着大地上任何一种生命的存在而感动。他还是一位彻底的素食主义者,这份执着和“怪癖”没有一点宗教色彩,因为他太喜欢绿色了,太向往绿色了,他虔诚地期望绿色生命永远的渗透着他的诗心,荡漾在他充满生命活力、绿意盎然的文章中。正是他对绿色生命的狂爱,他的文章才感动了许多读者。可叹的是,这位幸福地喜欢绿色生命的青年作家,于1999年才39岁就告别了一切,如一朵山花过早的枯萎在癌病的摧残中,在中国文坛曾掀起一阵悲哀。时至今日,也有不少怀念文章出现,一次又一次的感动着人们。他死后留下遗嘱,让他的朋友和亲人把他的骨灰撒在麦田里,让绿色继续渗透着他的另一个世界。
人与大自然中的一切生命同拥一个星球,这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幸福。可以想象人之初与大地上的一切生灵生生息息、相依相偎,那是多么和谐的景象。当人类直立行走和开始使用石器及火之后,人类文明便随着一星火花慢慢滋长。文明的产生自然把人与它类动物区别开来,贪婪和占有开始怂恿着人们把算计和利刀伸向它类动物。在杀戮和血腥中,曾经与人类共同出没于森林和洞穴的动物们开始让步,它们让到数量锐减,让到无处藏身,让到彻底灭绝。人类在长期的占有中,渐渐麻木了良知,漠视了它类动物的存在和眼神,只知道一味的享受和索取。但是它类动物却永远惦记着人类,它们始终怀想着曾经出入森林、河泽、草原的过去,永远把人类当着朋友。
2004年12月26日,距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北近海底下40公里,发生了一起里氏9级地震,震后海岸线猛然急退了近300米,然后又以每秒200米的速度轰然冲上苏门答腊岛的亚齐省海滩。一个小时后,滔天海潮登陆泰国南部,两小时后殃及印度斯里兰卡,使20000多人葬身海底。而在海啸向泰国南部海滩袭来时,有三个顽童还在海边惊呼扑天而来的海浪,这时一头平时在他们父母铁钩下搬运木头的大象,冲出椰树林,用长鼻一卷,救起了海滩上三个顽童,然后大步向椰树林走去。这是一个真实而感人的镜头,一直被新闻界追捧,一直感动着灾后的人们。还有海豚,这个大海的精灵,它多次救人的故事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早在公元前5世纪它救人的事就被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在他的日记里。而最著名的海豚救人事件发生在1959年夏天,“里奥·阿泰罗”号客轮在加勒比海遇难,许多乘客落水,这时几条大鲨鱼袭来,危急关头成群的海豚游来赶走了鲨鱼救起了大家。就在2008年8月28日,24岁美国青年托德·里德里斯在海边尽情的冲浪,玩得正兴起时,一头约4米长的大白鲨袭来咬住了他的右脚,就在托德即将命丧鲨口时,几只海豚围了上来,阻退了鲨鱼并将托德保护到它们中间,才使得托德逃回了岸边。面对这些真实的例子,我们应该停止对动物们的可耻算计,应该去拥抱它们,它们与人类同样是自然的主宰。
《圣经·创世记》却说:神按照自己的模样造出了人,并让人们全面管理鱼、鸟、牲畜以及地上的一切昆虫,还将遍地的种子、蔬菜及树上的果子统统赐予人类。这种说法无疑在教义上高高确立了人类是大自然的主宰,而今看来,这种主宰岂不是占有和破坏的近义。而在我们东方的《道德经》却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位两千多年前的老子李耳已告诉我们,大自然才是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让人敬畏的。事实上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从本质上而言,是对某种臆想的自然神的敬畏,这种敬畏还上升到宗教的层面。佛教是怜悯众生的从不杀生,包括花草树木,而是对世界万物怀着虔诚的感恩。我们永远是大地的婴儿,自然、生命、规律也使我们无法不越来越沉重地正视这些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迷茫中寻找到人类逐渐淡去的本身,才能明白生活而不只是为了活着,才能寻找到一条迈向远方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