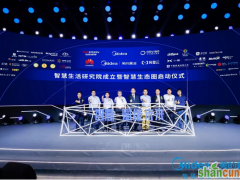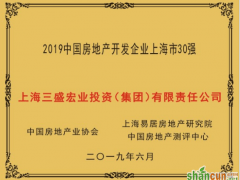“如果把微中心和节点城市的建设纳入都市圈空间规划,那么对于我们未来无论是都市圈的发展,还是城市群的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月27日,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进入第二天议程,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院长顾强出席“中国区域发展的都市圈时代”分论坛时如此表示。
都市圈提速
2019年2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经国务院同意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文中首次明确了都市圈的概念,并开创性地提出了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一整套解决方案,对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都市圈的建设作出了指导。
《意见》中对都市圈的定义是“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飞速推进,2018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8.3亿人,较1978年末增加6.6亿人,年均增加1644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9.58%,比1978年末提高41.6个百分点。但和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城镇化率仍处于较低水平。
根据国际经验,在城镇化水平达到70%之前,城镇化水平都会保持较快增长,预计我国城镇化率仍将在未来十年左右稳步提升。
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加快城市群建设发展,并确定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19个国家级城市群。2016年,占国土总面积14.7%的我国前十大城市群,以全国14.7%的人口数创造了全国76.6%的经济产出,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将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空间载体。未来,在培育壮大城市群过程中,以大城市、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将扮演“引擎”的角色。
在城市向大型化、中心化发展的同时,都市圈化已成为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的新特征。行政边界的限制逐渐被打破,各要素通过有序流动实现合理布局,人口、空间、产业等多个维度均呈现出都市圈化特征,高度网络化的城镇体系正在形成。
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数据表明,从中国都市圈主要经济指标占比来看,31个都市圈GDP占比达到47%,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以广州都市圈为例,2017年广州都市圈GDP总额约6151.35亿美元,在2017年全球主要国家GDP排名第22位,超过瑞典、波兰,可以说“富可敌国”。
都市圈是大企业的成长地和主要集聚地。从中国来看,世界财富500强企业88%分布在各省会及其紧邻的周边区域,仅有12家世界500强企业分布在非都市圈范围内,约70%左右企业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都市圈内,杭州都市圈汇聚了3家,其他都市圈集聚了14家。
顾强表示:“都市圈都是城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是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华夏幸福从固安发展壮大,得益于北京人口、产业等要素的外溢,这一案例是我们后续布局全国的重要参考经验。”
但需要正视的是,近年来,我国都市圈建设呈现较快发展态势,但城市间交通一体化水平不高、分工协作不够、低水平同质化竞争严重、协同发展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依然突出。
经验借鉴
我国都市圈建设起步晚,借鉴如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等成熟都市圈经验,总结共性规律,这是我国的后发优势。
都市圈由中心到边缘的最大半径往往决定于人们能忍受的最长通勤时间。研究发现,人们可忍受的最长通勤时间为45分钟到1小时,这就是所谓的“45分钟定律”。
实际来看,伦敦都市圈内绝大多数新城都分布在50公里圈层之内;巴黎都市圈内城镇也主要位于50公里圈层以内;东京都市圈半径从1960年的40公里发展到1995年的80公里,2015年拓展至100公里,但其DID(城市人口密集区)地区仍稳定在50公里范围,由此看来,都市圈的核心腹地范围稳定在1小时交通通勤范围内。
参照四大都市圈空间发展的经验值可知,空间连绵、联系紧密的成熟都市圈伸展半径稳定在50~80公里,面积大约1~2万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1000人/平方公里。都市圈的有效辐射范围最远不超过2小时通勤圈,空间面积一般也不超过2万平方公里。
伴随东京都市圈人口的持续增长和职住分离现象的不断增加,产生大量的通勤出行需求。轨道交通以其全天候、运量大、速度快、占地少,节能环保等优点,成为都市圈交通基础设施中的优先选项,支撑其高强度的通勤流。目前,东京都市圈的轨道交通出行比重已经高达58%,远高于其他都市圈,成为名副其实的“轨道上的都市圈”。
伴随人口产业不断向中心集聚,东京都市圈内部也出现用地紧张、人口拥挤、环境污染等发展问题。为了引导产业向外围转移,日本政府加速发展干线及市郊铁路,着力打造“地铁+市郊通勤铁路”的交通模式,在更大范围实现产业空间布局的优化,促使东京都市圈工业的空间分布沿交通干线向外生长,形成带状产业密集区。与此同时,轨道交通也加速了东京都市圈新城的形成与发展,引导人口不断向外围疏解。
伦敦都市圈新城建设走在世界前列,自1944年大伦敦规划提出在伦敦周围地区建设8个卫星城以后,到1974年,英国先后建立了32个新城。第一代新城主要是指1946~1955年间建设的新城,共有14个,其中8个位于大伦敦地区,此时新城定位实质是“睡城”,核心目的是疏散伦敦核心区的人口。第二代新城开发建设并不多,但定位逐渐趋于半独立职住结合的新城,开始注重功能的自我均衡。
第三代新城一般指从1967年起建立的新城,共确立了10个新城,其中弥尔顿凯恩斯、彼得伯勒和北安普顿均位于大伦敦地区,此时的新城建设已充分认识到了产业导入的重要性,继续强调经济对人口的承载作用,通过新城自身创造就业岗位,实现职住平衡。
在伦敦绿带空间建设过程中,大伦敦整体规划的出台和城乡规划法的颁布是保障绿带有效建设的关键,此后各地政府在其发展规划中均被要求编制绿带规划内容。此外,绿带政策也被引入到了法国的规划体系中。大巴黎政府通过建设5条绿带、发展郊区农业,整治郊区森林和绿地,实施绿色空间计划等一系列措施保护本地区自然环境资源,维护区域生态平衡,同时也为未来发展留下一定空间。
总体来看,国际都市圈的发展经验表明,都市圈空间范围通常以1~2万平方公里为有效辐射范围;都市圈可以轨交为主体构建一体高效的综合交通体系,强化内外交通联系,实现都市圈产业和人口的合理有序分布;通过科学定位、优势互补,进行区域产业分工协作,建立核心区功能有效疏解机制,解决“大城市病”,获得整体竞争优势;打破行政分割,协同保障都市圈生态系统意义重大;建立可操作的跨区域协商机制是落实都市圈发展重大事项的保障。
构筑微中心
顾强说:“都市圈是高度融合的网络状城镇体系,微中心是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都市圈与国际比较差距并不在核心区,而主要在微中心和节点城市上,以东京为例:50~100万级(人口)城市5个,20~50万级城市18个,5~20万级城市84个,而北京的相应数字分别为2个、7个和8个。因此,将节点城市、微中心建设发展纳入都市圈空间规划体系和范畴,促进都市圈空间体系结构的集约化和合理化,是都市圈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目前,我国都市圈节点城市、微中心发展严重不足,跨城交通建设非常落后。比如北京市郊铁路仅290公里,远低于东京4476公里、伦敦3076公里。而北京极端通勤平均需要72分钟,54%集中在北三县。顾强认为,解决之道在于以公共交通导向的开发模式(TOD)和社会服务设施建设为导向的开发模式(SOD)建设微中心,优化都市圈空间结构。
顾强表示,无论是伦敦新城建设,还是东京新城发展,都是按TOD和SOD理念建设,我国应在推进TOD的同时,倡导SOD理念,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共享机制,促进产城融合发展。具体层面,发展多层次、多模式、多制式无缝连接的综合交通系统;构建以城际铁路、市郊铁路和市域轨道为主体覆盖都市圈的综合交通网络;推动基础设施交通互联互通,以消除断头路为突破口,完善区域高速公路网。
在以固安产业新城项目为典型案例的这种开发性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中,社会资本自身具有造血功能,负责整个新城新区的规划设计、开发建设、产业发展、城市运营,政府主要负责顶层设计、行政审批、维护秩序、公共服务监管等事务,不新增政府债务,合作期结束后,所有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移交政府。这是PPP模式的一种创新与探索。
顾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华夏幸福从固安发展壮大亦得益于北京人口、产业等要素的外溢,这一案例也是企业后续布局全国的重要参考经验。目前华夏幸福已经围绕北京、上海等15大都市圈核心城市辐射的外溢圈层布局产业新城,享受了都市圈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外围节点性城市价值提升红利。”
如今都市圈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政府引导下,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有利于形成都市圈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在当前金融攻坚战和去杠杆的背景下,都市圈开发建设融资渠道收窄,亟须进一步拓宽融项目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方式。通过PPP模式、资产证券化、融资租赁等渠道,引入社会资本参与都市圈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新区新城建设,可以降低政府负债风险,完善都市圈城镇体系,提升外围地区城镇化水平。顾强最后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