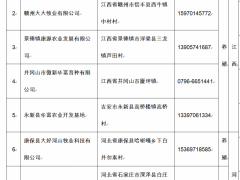被大家和生产企业宣传为类似人类艾滋病那样的蓝耳病真是当代猪病的元凶吗?非接种疫苗不保吗?笔者与许多养猪人的实践证明,猪群发生了蓝耳病,只要将猪群放归大自然,让它们呼吸大自然新鲜的空气,让它们有足够的领地自由活动,让它们拱拱土、晒晒太阳,让它们接触草木,十天半月,那些被大家们宣判死刑的猪群却获得新生。这种治疗方式或许并不适合集约化养猪的模式,但它至少给人们启示:蓝耳病并没有人们宣传的那么可怕,环境调节疗法都可以治愈的事实直指该病毒是一种条件性或机会性的病毒。条件性疾病的预防真需要疫苗吗
在疫苗业的顶层设计中首先要考量什么疫苗该做,什么疫苗不该做。正是在这种逢病就做疫苗的错误指导下,许多猪场在接种蓝耳病疫苗后爆发了蓝耳病。
艾滋病可怕,即或将来有了疫苗,也不必人人接种吧!因为只要洁身自好,不接触血液制品的注射就不会染病。作为养猪业更没有必要逢病就做疫苗,人们更应该思考这些条件性传染病发生的环境条件因素,切实规避之。
谁也无法预料,世界猪群这个系统的进化将来会呈现多少以往未出现的疾病。如果以近30年呈现了蓝耳病,圆环病毒病两种病的速度计,假设未来的60年再呈现4种传染病,每病必做疫苗、必接种的话,加上现有的疫苗接种,猪群何忍以堪更何况这些所谓的新病原未必真新,它们极有可能与猪群已经共同进化了千万年,只是人们未发现而已。之所以应时而出皆因猪群系统进化,猪群防卫能力下降的必然结果。
而以上各种现象均是人类乱作为的报应。
1.盲目加大接种剂量
猪瘟疫苗接种后效果不理想,便加大接种剂量。认为普通苗的750个兔感染单位太少,故而生产含有7500兔感染单位的浓缩苗,更有甚者,ST传代苗含量高达15000-30000兔感染单位。如果说这类疫苗真能扑灭猪瘟也罢,遗憾的是,笔者见到不少接种这类疫苗的猪群,相关抗体水平依旧不达标。回想笔者在20世纪60年代制作猪瘟湿苗,当时只能依据接种兔的体温曲线来决定苗材的取舍与否,到基层的冷链也不如今天,接种到猪的剂量未必就有750个兔感染单位,但绝大多数接种猪都能免于猪瘟感染。这无疑反佐盲目加大疫苗接种剂量有失偏颇,其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思考。
2.盲目加大接种频率
猪伪狂犬病疫苗,由最初的1年2次接种演变为现在1年3次,有的疫苗生产企业更是鼓吹1年接种4次,可是效果又如何呢?这不得不让人想到一个经典的营销案例,那是讲一个牙膏厂的老板为增加销量犯愁,一个营销员见状便献策,何不将牙膏的出口孔径做大1倍,销量不就翻了1倍了。这与增加接种次数不是同出一辙吗?看似无可挑剔,增加接种次数之妙计果然肥了企业,却并未安养猪业之天下。
3.全国应该有统一的免疫程序
当今,免疫程序随心所欲,五花八门,乱象丛生。提出全国应该有统一的免疫程序,就有人以高科技检测结果不同为由否定之,认为这是脱离实际情况的教条。不妨先通过比较医学看人医是如何做到的。我国人类计划免疫(PI)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其做法是在7岁前用四苗防六病,即接种卡介苗(BCG)、脊髓灰质炎疫苗(OPV)、百白破联合疫苗(DPT)、麻疹疫苗(MV)来预防结核、脊髓灰质炎、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和麻疹。现在又扩大计划免疫(EPI),在PI基础上增加乙肝、风疹和腮腺炎疫苗。无论是PI还是EPI,免疫程序全国是统一的,没有地域人群的区别。不否认猪群之间的差异,特别是母源抗体的差异,但是可以依据检测指标拟定2-3种全国统一方案,择其相应者,其中最广为应用的方案是主导方案。人们在选择非主导方案时不要一用了之,而是要深刻反思,为什么猪群不能接受主导方案,找到原因改进之,最后回归到主导方案方是务本。
4.审批进口外国疫苗不慎重,甚或太放肆
众所周知,疫苗毒是一种活的生物,如果国内不存在这种毒株,那么引进这类活疫苗无异于引入新的物种。这应该是真正的“生物安全”问题。如果坊间传闻的某外国疫苗企业最初引进的蓝耳疫苗的毒株是我国没有的欧洲株一事属实,那么审批引进的相关人员要么视民族大义之不顾而太恣意妄为,要么就是太无知无识无能。孔子告诫:“不二过”。故而,我们再引进或使用国外疫苗过程中要尤为慎重。
5. 兽用生物制品走私严重
兽用生物制品走私极其泛滥,从流行性腹泻疫苗、伪狂犬病疫苗、圆环病毒病疫苗、卵黄抗体等等,都有多国的走私产品入境,一些走私制品是通过知识层或学院派的留学人员或在国外进修、工作的人员通过非法途径入境牟取暴利,不仅造成海关关税的流失,更为严重的是对中国养猪业的生物安全形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