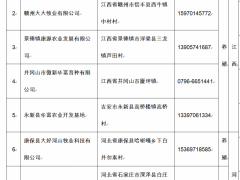在长江上游生态涵养区的云贵高原,“深度贫困县”集中。连日来,记者走村串户,一窥我国脱贫“最后一公里”的攻坚进展。
金沙江上游的云南丽江是记者此次“长江行”的首站。在去玉龙县鲁甸乡的路上,海拔2000米的高原风光令人赞叹,但一路颠簸、山高弯急的生存环境,又让人心生脱贫之忧。
脱贫不能光喊口号,要靠特色产业带动。鲁甸乡的办法是通过土地流转,成立专业合作社,扶助77户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发展“云南白药”种植园。“过去是在坡地种粮,没得多少收入。”太平村大水沟组村民和仕珍说,有了扶贫政策,有了建房补助,又种上中药材,她家2015年底实现了脱贫。
因为青山绿水的滋养,云贵高原不少地方瞄准“以茶脱贫”。在“贵州茶叶第一县”遵义市湄潭县,60万亩茶园高低错落、郁郁葱葱,著名的“遵义红”“贵州针”就产于此,全县茶产业综合收入超100亿元。
“天上下多大,地上流多大,顿顿红苕苞谷饭,吃水要翻几匹山。”说起湄潭县核桃坝村的“以茶脱贫”史,支部书记陈廷明感慨万千。前些年靠种茶实现了脱贫,近年来村里升级推动“茶旅一体化”富起来,还解决了3000余名外来务工人员就业。2017年全村人均收入达3.16万元,人均年分红金额超过2000元。
核桃坝村是贵州“种茶脱贫、茶旅致富”的一个缩影。到去年,贵州茶叶种植面积达700万亩,成为中国茶叶种植面积最大的省份。
脱贫要有资源,才能把资源变产业。但“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怎么办?一个字:搬。
云南昭通市位于金沙江下游,是长江上游最后一道生态保护线。市委书记杨亚林的介绍令人吃惊:全市人均耕地不足一亩,但人口密度却是全省的2.23倍!11个县区只有水富不是贫困县,贫困人口多达92.1万!
“只有异地搬迁,才有可能弯道超车。”杨亚林说,开始是分散搬到附近的岭坡、村落,但发现效果不彰,近年来干脆提出“进城入镇、进厂上楼”。这叫既“挪穷窝”又“拔穷根”。
但故土难离。绥江县干部聂晓梅说,县里要求每位干部联系五户左右,问计于民,同吃同住同讨论,直到搬出来。
“搬出来”只是第一步,如何“稳得住”更难。昭通市的办法是:近抓打工就业,远抓产业培育。
绥江县鲢鱼村是一个农户搬迁安置点。下山后,曾经的贫困户于富贵住上了白墙灰瓦的川南民居,靠县农业局培育的“半山红”李子树脱了贫。“一亩李子收入5000块,家里有七八亩呢!”在场的绥江县委书记杨淞说,去年全县李子产量4万吨,产值2亿元。
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精准脱贫进入“倒计时”,少数地方不免焦虑,脱贫工作走样变形。在一个乡镇,记者看到脱贫展板做得很精美,书面措施全是“四个A”“八个B”,八股文气息重,形式大于内容。有个县一种特色农产品仍然局限在种植环节,没有加工环节作缓冲带,农旅融合的田园综合体也没起步,但种植面积过大,很容易陷入“丰产不丰收”。还有个乡镇只是把贫困户交给一家企业,没有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干部在动、农民不动”。
精准脱贫贵在“实干”,下足“绣花功夫”,做“虚功”害人又害己。在采访中,还有的干部认为2020年是全面脱贫“大限”,无论如何当地贫困户一定会被“摘帽”,这样的声音在基层出现令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