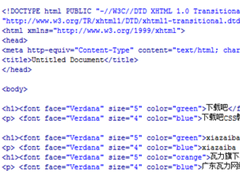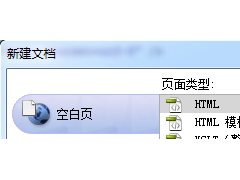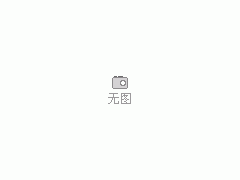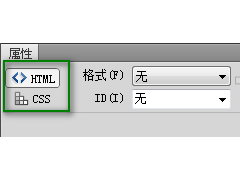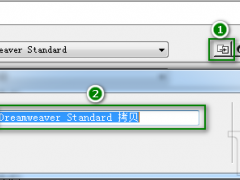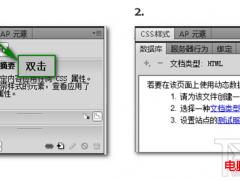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
【提要】
苏秦为燕国奔忙游说、劳苦功高,但却在国内受到谗言的陷害。苏秦只有坦诚表白自己、对那种以礼仪信用来攻击他的论调针锋相对才可以在燕国站得住脚。让我们看看苏秦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
【原文】
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万乘下之,尊之于廷,示天下与小人群也。”
武安君从齐来,而燕王不馆也。谓燕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见足下身无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于郊,显臣于廷。今臣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听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伤臣于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 ,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
苏秦曰:“且夫孝如曾参,义不离亲一夕宿于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齐?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污武王之义而不臣焉,辞孤竹之君,饿而死于首阳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数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来,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扬燕、秦之威于齐而取大功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皆自覆之术,非进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兴,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为可乎?则齐不益于营丘,足下不逾楚境,不窥于边城之外。且臣有老母于周,离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术,而谋进取之道,臣之趣固不与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仆者进取之臣也,所谓以忠信得罪于君者也。”
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
对曰:“足下不知也。臣邻家有远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归,其私之者忧之。其妻曰:‘公勿忧也,吾已为药酒以待之矣。’后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进之。妾知其药酒也,进之则杀主父,言之则逐主母。乃阳僵弃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弃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于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适不幸而有类妾之弃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义益国,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后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说齐,曾不欺之也。使之说齐者,莫如臣之言也,虽尧、舜之智,不敢取也。”
【译文】
有人对燕王毁谤苏秦说:“苏秦是天下最不讲信义的人。大王以万乘之尊却非常谦恭地对待他,在朝廷上推崇他,但这是向天下人显示了自己与小人为伍啊。”苏秦从齐国归来,燕王竟然不给他预备住处。
苏秦对燕王说:“我本是东周的一个平庸之辈,当初见大王时没有半点儿功劳,但大王到郊外去迎接我,使我在朝廷上地位显赫。现在我替您出使齐国,取得了收复十座城邑的利益,挽救了危亡之中的燕国,可是您却不再信任我,一定是有人说我不守信义,在大王面前中伤我。其实,我不守信义,那倒是您的福气。假使我像尾生那样讲信用,像伯夷那样廉洁,像曾参那要孝顺,具有这三种天下公认的高尚操行,来为大王效命,是不是可以呢?”燕王说:“当然可以。”苏秦说:“如果真是这样,我也就不会来为大王服务了。”
苏秦道:“臣要像曾参一样孝顺,就不能离开父母在外面歇宿一夜,您又怎么能让他到齐国去呢?像伯夷那样廉洁,不吃白食,认为周武王不义,不做他的臣下,又拒不接受孤竹国的君位,饿死在首阳山上,廉洁到这种程度,又怎么肯步行几千里,而为弱小燕国的垂危君主服务呢?如果臣有尾生的信用,和女于约会在桥下,那女子没来,直到水淹上身也不离开,最终抱着桥柱被淹死。讲信义到这种地步,怎么肯到齐国去宣扬燕秦的威力,并取得巨大的功绩呢?再说讲信义道德的人,都是用来自我完善,不是用来帮助他人的。所以这都是满足现状的办法,而不是谋求进取的途径。再说,三王交替兴起,五霸相继兴盛,他们都不满足现状。如果满足现状是可以的,那么齐国就不会进兵营丘,您也不能越过楚国边境,不可能窥探边城之外了。况且我在周地还有老母,离开老母来事奉您,抛开固步自封的做法,谋求进取的策略。看来我的目标,本来不和您相同。大王是满足现状的君主,而我是谋求进取的臣子,这就是因为忠信而得罪于君主的原因啊。”
燕王说:“忠信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苏秦说:“您不知道,我的邻居中有个在远地方做官的人,他的妻子跟别人私通。她的丈夫眼看就快要回来了,和他私通的人很忧虑。那妻子对他的情夫说:‘你别担心,我已经准备了毒酒等着他呢。’过了两天,丈夫到家了,妻子让女仆捧着毒酒送给他丈夫。女仆知道那是毒酒,如果送上去就要毒死男主人,如果说出实情女主人难以避免被赶走。于是她假装跌倒,泼掉了毒酒。男主人很生气,就用竹板打她。那女仆这一倒,对上救了男主人,对下保住了女主人。忠心到了这种地步,然而仍然免不了被打,这就是因为忠信反而受到罪责的人啊。现在我的处境,恰恰不幸和那个女仆泼掉毒酒反而受罚的遭遇类似。而且我事奉大王您,尽量使信义崇高,国家获益,如今竟受罪责,我担心以后天下来事奉您的人,没有谁自信能够做到这样。况且我劝说齐王,确实没用欺诈的手段,只不过游说齐国的其它使者,没有谁像我说得那么婉转。即使他们像尧、舜一样贤明,齐国也不肯相信他们的话。”
【评析】
苏秦通过列举尾生、伯夷、曾参的事迹,和一个小故事,驳斥了那些道学家们对他的指责,也说明了自己好心没有好报的处境。道学家们实际上不懂政治,正象马基雅维利将政治科学从旧道德中分离出来一样,苏秦也指出政治活动不能用普通的仁义道德来评价,如果政治活动受到高尚道德的制约,那么政治上将一事无成、毫无作为。国家与个人不一样,国家之间由于无信义可言,就必须讲实力、讲策略、讲变通。国家之间是超越于日常道德的,所以被日常道德所不齿的威逼利诱、暴力欺诈会经常使用,不足为奇。阴谋诡计用在日常人事上,那是小人伎俩,而如果用在国家大事上,那是枭雄志士的雄才大略。何况苏秦等人违背日常道德完全是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了个人的清名或利益。
其实战国时期之所以繁荣,战国策士们之所以功勋卓著,在于当时儒家思想还没有占居主流,在于策士们重功利而不重清名的功利主义人生观。儒家强调高行节义,但因此导致道德至上的虚骄之气充斥官场和社会中,而战国策士们的务实精神为国家增添了活力。善变敢说、运筹谋划不是在扭曲人性,而是在充分张扬人的智力、个性和气度,显露出人之为人的生命的力量和存在的价值。以辞锋相争,以智谋相夺,没有遮蔽道德虚饰的战国策士们的这种进取有为的功利主义人生观,在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那些蒙蔽燕王的士大夫和卫道士们,标榜高行节义,却由于囿于教条而不能成事,困于日常道德而不能处理国际事务,甚至有的虚伪透顶,明里拿道义作攻击人的幌子,暗里玩弄权术诡计、大行尔虞我诈之本领。对一个国家来说,有害倒是这类人。